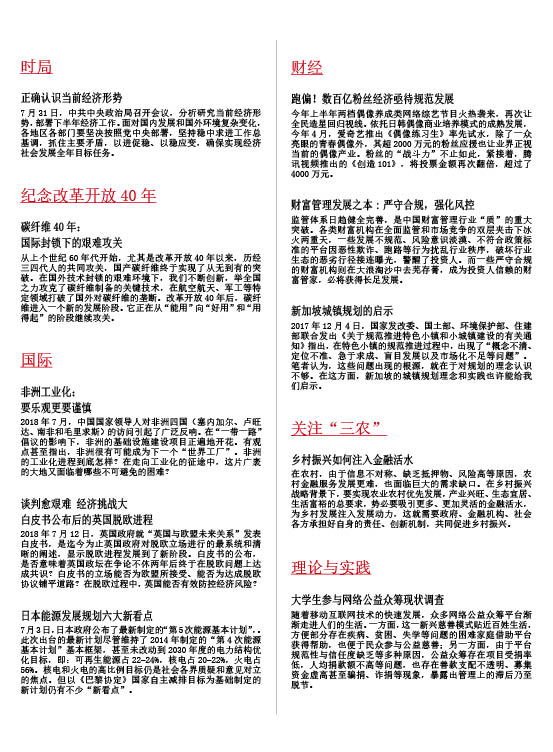
非洲工业化:要乐观更要谨慎
2018年7月,中国国家领导人对非洲四国(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和毛里求斯)的访问引起了广泛反响。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表示,中国为非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也为该地区各国的融资提供了便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遍地开花,有关非洲地区工业化的讨论再次得到广泛关注。有观点甚至指出,非洲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作为占全球总陆地面积20.4%、拥有约12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洲,非洲的工业化进程到底怎样?在走向工业化的征途中,这片广袤的大地又面临着哪些不可避免的困难?

工业化水平长期落后
“实现工业化”一直是非洲各国多年的夙愿,这种愿望与呼声在中国高层领导对非洲进行访问后尤其明显。一方面,中国长期积极投资非洲的跨国、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无疑将为非洲实现工业化提供运输上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大多数工业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产能过剩情况,希望向国外转移产能,并把非洲作为重点转移对象。对非洲国家而言,这是其进行产业分工业链建设的良好机遇。
中国2016年在非洲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7 年) 《经济》制图
要实现工业化,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工业化,非洲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又是怎样的。
“工业化并不是单纯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它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和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黄群慧指出,工业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在国民收入中,工业活动所占比例逐步提高,甚至占主导地位;制造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二次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呈现增加趋势;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即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国内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一般可以将工业化进程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五个时期。世界上一些很落后的、还没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属于前工业化阶段。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中期或后期。”黄群慧这样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李智彪也告诉《经济》记者,非洲各个国家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从整体来看,“目前一个真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没有”。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在非洲大陆55个经济体中,仅有3个国家跨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20个国家属于“发展中工业经济体”,32个国家属于“工业最不发达国家”。
非洲工业化的落后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制造业产值低、制造业就业人口和中高端技术制成品出口少。数据显示,2014年,非洲制造业增加值占非洲GDP的10.1%,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6%;2013年,该地区制造业就业人口仅占非洲就业人口总数的10.7%;制成品出口占非洲商品出口总额的47%,占全球制成品出口总额的2%,且其出口的制成品主要是资源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8年的十余年间,非洲经济曾持续快速增长。随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陆续到来,快速增长的趋势被阻断。2014年下半年开始,以石油为主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连续暴跌,对该地区经济产生巨大冲击。非洲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受到明显影响。
“作为现代国家的支柱产业,工业不仅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工具和技术装备,也为大众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工业化是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持续扩张,进而带来农业部门净产值和劳动力比重的持续下降,最终令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过程。”李智彪这样告诉《经济》记者。
近代以来,全球各国均把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之一。非洲也不例外,其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启了对工业化的探索。遗憾的是,半个世纪以来,非洲大陆仍是全世界工业化最落后的地区。
优势掩盖下的无奈
提到非洲走工业化道路的优势,有两点不能不说。
这片大陆几乎拥有工业化所需的各种原材料。非洲已经探明石油储量约1200亿桶,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0%、总产量的12%;是世界六大产油区之一,也是近年来石油储量和产量增长最快的地区,被誉为“第二个海湾地区”。非洲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约15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总储量的8%左右。非洲的黄金、钻石、钴、铬、铂、银、磷酸盐、铀和铜等珍稀矿物质的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非洲还是全球可可、咖啡、天然橡胶、油棕、剑麻、丁香、花生、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地;非洲的渔业、畜牧业资源也相当丰富。
劳动力资源是另一个明显优势。2010年,非洲人口就已经达到10.32亿人,其人口构成特点突出表现在两方面:明显的年轻化、自然增长率高。2012年数据显示,在非洲全部人口中,14岁以下的人口约占40%,15岁到64岁的人口约占56%,65岁以上的人口仅占4%左右。2000年-2005年,非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5%;2005年-2010年为2.4%。另外,随着非洲国家对教育的不断投入,劳动人口的素质也在不断上升,高技术的人才和专家并不在少数。
然而,非洲走向工业化道路的阻碍恰恰也隐藏在上述表现中。
李智彪告诉《经济》记者,从整体上看,非洲大陆的自然资源确实丰富,但从国家角度看,工业化进展较快的恰恰是矿产资源较少的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塞内加尔。资源丰富意味着工业化潜力较大,但有些非洲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动力不是很强,比较依赖初级原材料的出口;尤其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时期,上述倾向就更加明显。
通常,大家也都认为非洲的人力成本较低,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想象中高。李智彪长期在非洲和中国一些地区进行调研,对比后发现,不少非洲国家如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一些城市企业职工的月薪比中国的城市,比如东莞,还要高。
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梁海明也告诉《经济》记者,有些非洲地区“再投资”的意识不强。企业一旦拿到钱,倾向全部拿来发放福利,而非用在刀刃上。另外,非洲国家整体上对“工业化”这件事儿比较着急,希望实现弯道超车。
“西方国家搞工业化,用了一百几十年的时间。非洲就想,要是自己也按部就班,还要一个多世纪才能完成工业化,耗时太久。他们就希望跳过工业化的初期,搞好服务型行业,但是没有工业做基础直接开拓服务业是很难的。因此,太过着急反倒更慢了。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对工业化的追求本身就不是很强烈,比如塞舌尔、毛里求斯,他们更希望发展旅游业和现代化农业。”梁海明这样说。
此外,曾经被殖民的历史,也是横亘在非洲与工业化之间的一堵高墙。
在非洲,多数国家接受殖民统治的时间比建国时间还要长。殖民统治令该地区各国在政治制度、语言文化、边界划分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和分歧。非洲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甚至比不上其与前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尽管非洲也存在区域合作组织,该地区的市场仍处于割裂状态,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并不十分活跃。
非洲进出口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非洲55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只有1700亿美元,约占该地区总出口额的15%,同一时期,亚洲国家、欧洲国家的数据分别为58%、67%。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预测,如果能够取消非洲内部的进口税,该地区的贸易额将提高53.2%。
选择怎样的工业化模式
如果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哪一条才是最适合非洲的呢?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梁益坚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动非洲工业化发展,一方面需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粮食的基本自给;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从传统部门逐渐转移到现代部门。其中,现代农业、日常消费品进口替代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人力资本培育是值得关注的4个重点领域。
1995年以来,非洲经济之所以实现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新兴经济体经济腾飞,带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疲软,石油、黄金和咖啡等多种非洲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造成非洲国家经济增速不断下降。
梁益坚强调,在经济全球化与分工国际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工业竞争非常激烈,无论是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市场规模等宏观领域,还是在人才资源、资金、技术、制度建设等微观领域,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非洲均处于不利位置。
“为摆脱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非洲需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而言的,传统工业化多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而新型工业化强调发挥现代科技在工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做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梁益坚这样说。
不过,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查道炯教授则对《经济》记者表示,他不认为非洲各国之间存在一个统一的工业化模式,原因就在于该地区国家情形各异。
“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用‘后发优势’解释非洲国家在工业化中的竞争力,这个逻辑存在过于直线推断的风险。分析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至少要弄清楚以下问题:这些国家的工业品消耗能力如何;如果能力不行,销往其前殖民宗主国是否可行。另外,如果中国企业参与其中,在非洲国家内需不足的时候,工业品返销中国是不是一个选择?一些观点认为,欧美设计+中国设备/管理+非洲劳动力生产+最终消费在欧美和日本,这种路径会适合非洲,但它是不是纸上谈兵呢?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谨慎的思考和调查。”查道炯认真地说。
查道炯还告诉记者,在参与非洲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在非洲制度和法律范围内维护自身权益,尤其是国有企业,不能因为没有资金来源的压力就忽视营利。
链接:非洲相关工业发展政策
目前在非洲,非盟、各次区域组织、各国均出台了推动工业发展的政策与战略。
大陆层面:非盟《2063年议程》提出七大愿景,非盟大会通过的旨在推动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加工业发展的《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
次区域层面:东非共同体2012年制定的工业化战略和政策、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2015年通过的《南共体工业化战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西共体2016-2020年战略框架》草案和配套战略行动方案等。
国家层面:几乎每个非洲国家都有旨在推动工业发展的规划,典型的如南非的《新增长路径发展战略》、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可持续的社会经济转型议程》、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经济恢复与发展计划》、尼日尔的《第二期复兴计划(2016-2021)》、肯尼亚的《2030年远景规划》、坦桑尼亚的《坦桑尼亚国家发展愿景2025》、刚果(金)的《减贫和增长战略》、喀麦隆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战略(2010-202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