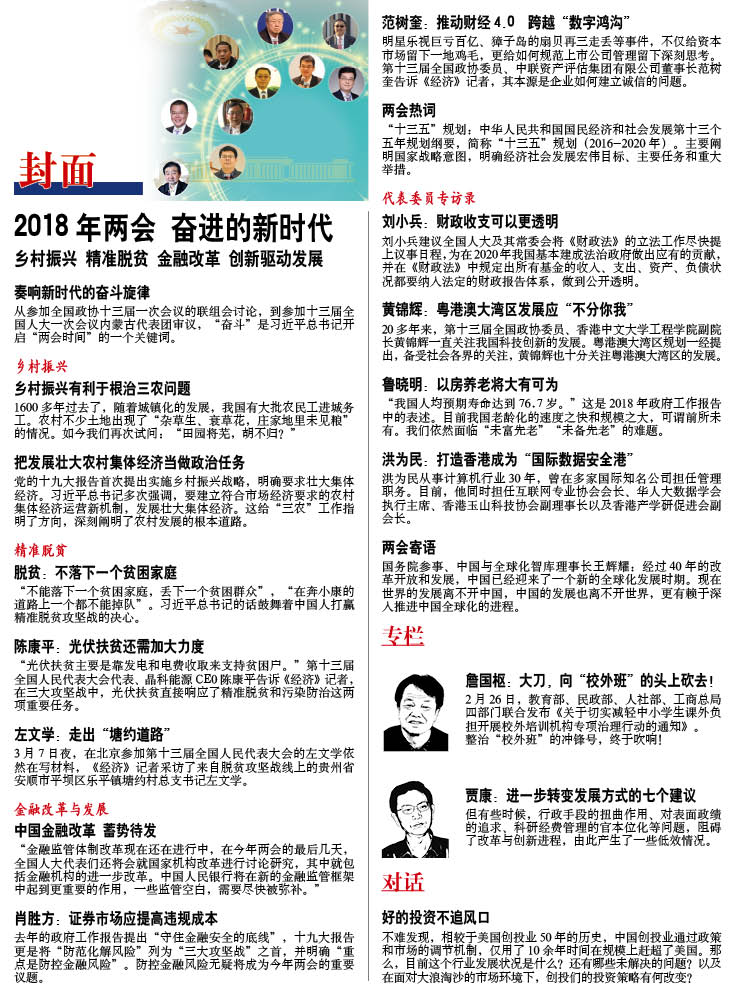
鲁晓明:以房养老将大有可为
——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 黄芳芳 摄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7岁。”这是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目前我国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可谓前所未有。我们依然面临“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难题。
“养老问题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以房养老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鲁晓明告诉《经济》记者,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老人住房自有率极高。针对房屋的高价值性和弱流通性特点,设计以实现有效融资为目的的以房养老产品是解决养老危机的必由之路。
以房养老不只有住房反向抵押
在鲁晓明看来,以房养老是利用房子的远期价值弥补养老资金的不足。在实践中,它有多种形式:租房养老、售房养老、房屋信托、住房反向抵押等等。
上述四种形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租房养老和房屋信托的主要问题是老人不能在此居住,房子少的老人的居住水平会下降。售房养老,可以保留居住权,但障碍是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居住权,只能通过合同来解决。而合同最大的风险是无法对抗第三人。住房反向抵押,既可以获得现金流,也可以在被抵押的房屋居住。国外的住房反向抵押规定老人的年龄起点为60岁-65岁不等。住房反向抵押更适合“资产富翁,现金穷人”这类老人。
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都在探索住房反向抵押。从实践效果来看,除了受“房产留给子女”的观念制约以外,以房养老的产品设计,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导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实施住房反向抵押的效果不佳。相反,日本的探索逐渐有了起色。
鲁晓明指出,很多人将以房养老等同于住房反向抵押,但这是不准确的。香港和新加坡的住房反向抵押最大的问题在于产品本身缺乏吸引力。由于人的预期寿命具有不确定性,有可能老人从机构获得的钱超过房产价值。在新加坡,如果机构付给老人的金额超出了房产价值,机构会向老人索要多给付的资金。同时,产品设计的条件也十分苛刻。
以房养老推进难的根源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了以房养老的探索。尤其是2014年中国保监会出台《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肯定了以房养老中住房反向抵押保险的意义,并决定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展住房反向抵押保险试点。在实践中,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以房养老试点,形式包括住房反向抵押、售房养老、租房养老等,但试点效果均不理想。
“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杂糅在一起。”鲁晓明指出,一是,在法律层面,房屋的远期预期不明朗,房屋所有权受制于土地使用权年限的限制。二是,产品本身的风险控制机制尚未健全。三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没有相关稳定的法律制度,目前主要靠政策调控,因此远期的房产价值难以控制。最后,银行或保险公司实行的年度考核制度也使业务人员缺乏推销产品的动力。
然而,荷兰的以房养老实践颇具成效,让很多老人提高了生活质量。“除了养老金,还有以房养老的钱,老人仍可以住在房子里。他在百年以后,房子的价值也实现了。”鲁晓明说。
“未来,以房养老大有可为。它可以帮助国家解决一部分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以房养老的障碍,鲁晓明建议,一是,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将盘活资产,自我筹措资金作为移风易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府、媒体、教育机构等多方协作,大力宣传以房养老对于老年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在全社会达成以房养老的共识。
二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首先,稳定房地产预期,修改《物权法》中关于土地使用权70年期限的规定,构建长效住房产权机制。其次,利用民法典编撰的有利契机,规定居住权制度。允许老年人以低于房屋价值出售房屋,但保留居住权至去世之时,以在实现以房融资之时,亦不至于因出售房屋而失去基本居所;允许老年人以获取居住权这一较低投资方式投资分时度假酒店、异地房产,避免单一异地购房这一高昂的候鸟式养老方式,实现以较小的投入达到异地养老之目的。再次,利用民法典编撰的有利契机,创新农村房屋流转制度,为未来实现农村房屋的流转创造条件,为农村房屋纳入以房养老消除制度障碍。最后,利用民法典编撰的有利契机,规定反向抵押权。
三是,出台专项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政策,加大对住房反向抵押等以房养老产品的支持力度。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住房反向抵押、售房养老等产品的免税措施,对于参与以房养老的房产给予免税或减税支持,切实减轻以房养老产品成本;对于风险较大的以房养老产品,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切实减轻以房养老产品的风险,刺激金融机构开发以房养老产品的积极性。
《经济》记者直击两会热点问题,两会记者邮箱:
黄芳芳:hff_1983@163.com;寇佳丽:jiali_kou@vip.126.com
沟通交流平台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