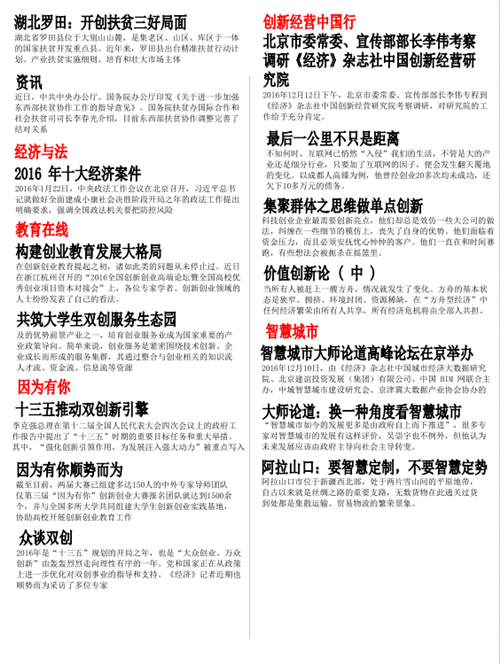
价值创新论(中)
本文主要探讨新环境下宏观经济层面的创新问题。首先是认知的革新。美国学者乌麦尔·哈克创造出两个新词——方舟型经济和狩猎型经济,以描述今天以前的商业和今天往后的商业。他称以前的商业是“狩猎型经济”,其经济规则是一群猎手(企业)在圈定的某片猎场(行业或目标市场)中狩猎(经营)。在某次狩猎活动中,最强悍、最有经验、装备最佳的猎手猎获过人(利润);从总体来看,当一片猎场中的猎物骤减时,猎人们便开始转场,他们并不担心来年的生计,因为那时的猎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猎物会源源不断地再生出来。
当所有人被赶上一艘方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方舟的基本状态是狭窄、拥挤、环境封闭、资源稀缺,在“方舟型经济”中,任何经济繁荣由所有人共享,所有经济危机将由全部人共担。所以,无论做什么,首先必须保护资源,尽可能减少损耗。进一步的要求是,高效利用资源,不仅利人利己,还要有利于未来的人们。
其次是制度的创新。当经济由“狩猎”向“方舟”转变时,使得原本隐藏在社会、经济深处的善恶关系显现出来。据统计,自2015年6月起,险资举牌金额已超过1700亿元,涉及上市公司达到了37家。自2015年夏季“宝万”之争公开化以后,二级市场上的险资异常兴奋,张开大口朝向了中国最优秀的实体企业(如格力、伊利、南玻等)。12月3日,证监会高层发声,警告资产管理人“不应当做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应当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应当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更不能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根本不是金融创新,而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此番证监会发声,意味着在方舟型经济下,社会、政府管理机构对市场上的“恶”行为(如过度消耗、热衷山寨、恶意收购、非循环经济)有责任作出反弹,并组织狙击。这种做法刚好应和了近几年市场自由化国家反思传统经济学的热潮。如宏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逊说:“当下,我们最明显的错误莫过于轻信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以为经济真的可以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再如奥巴马的经济顾问萨默斯也认为“大多数经济理论已经到了要再推敲、重思考的地步”。
此外,还要思考管理的创新。在狩猎型经济下,对行业或跨行业的管理大体是一件任其自然的事情;到了方舟型经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举个例子,最近十多年,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ics)大行其道,它指的是一种虚拟(如淘宝)或真实(如苏宁电器)的交易空间。该空间本身不生产产品,但能促进供求之间的交易,凭藉收取双方费用或赚取差价而获利。平台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过度经营。从表面上看,一个巨大销售平台的存在,吸引了众多提供产品的生产厂家和大量需要该类产品的消费者,使得供需双方达到平衡,也令经营者获得丰厚利润。从理论上讲,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令参与交易的各方和谐发展。但事实上,由于社会管理职能的缺失,平台经营者的过度经营,往往会引发“店大欺客”的现象。例如,占据了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和平台经营者,难免抬高市场进入的门槛、肆意压低一类商品的销售价格,甚至长期扣押应付货款。结果众多生产厂家丧失了市场话语权和自由创意空间,关连的商业生态变得单一、单调,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权力被压缩到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而创新的管理,就是要把市场从“一家独大”的状态下解脱出来,逐渐走向多元共生。(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 陈 钢)
当所有人被赶上一艘方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方舟的基本状态是狭窄、拥挤、环境封闭、资源稀缺,在“方舟型经济”中,任何经济繁荣由所有人共享,所有经济危机将由全部人共担。所以,无论做什么,首先必须保护资源,尽可能减少损耗。进一步的要求是,高效利用资源,不仅利人利己,还要有利于未来的人们。
其次是制度的创新。当经济由“狩猎”向“方舟”转变时,使得原本隐藏在社会、经济深处的善恶关系显现出来。据统计,自2015年6月起,险资举牌金额已超过1700亿元,涉及上市公司达到了37家。自2015年夏季“宝万”之争公开化以后,二级市场上的险资异常兴奋,张开大口朝向了中国最优秀的实体企业(如格力、伊利、南玻等)。12月3日,证监会高层发声,警告资产管理人“不应当做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应当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应当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更不能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根本不是金融创新,而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此番证监会发声,意味着在方舟型经济下,社会、政府管理机构对市场上的“恶”行为(如过度消耗、热衷山寨、恶意收购、非循环经济)有责任作出反弹,并组织狙击。这种做法刚好应和了近几年市场自由化国家反思传统经济学的热潮。如宏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逊说:“当下,我们最明显的错误莫过于轻信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以为经济真的可以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再如奥巴马的经济顾问萨默斯也认为“大多数经济理论已经到了要再推敲、重思考的地步”。
此外,还要思考管理的创新。在狩猎型经济下,对行业或跨行业的管理大体是一件任其自然的事情;到了方舟型经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举个例子,最近十多年,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ics)大行其道,它指的是一种虚拟(如淘宝)或真实(如苏宁电器)的交易空间。该空间本身不生产产品,但能促进供求之间的交易,凭藉收取双方费用或赚取差价而获利。平台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过度经营。从表面上看,一个巨大销售平台的存在,吸引了众多提供产品的生产厂家和大量需要该类产品的消费者,使得供需双方达到平衡,也令经营者获得丰厚利润。从理论上讲,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令参与交易的各方和谐发展。但事实上,由于社会管理职能的缺失,平台经营者的过度经营,往往会引发“店大欺客”的现象。例如,占据了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和平台经营者,难免抬高市场进入的门槛、肆意压低一类商品的销售价格,甚至长期扣押应付货款。结果众多生产厂家丧失了市场话语权和自由创意空间,关连的商业生态变得单一、单调,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权力被压缩到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而创新的管理,就是要把市场从“一家独大”的状态下解脱出来,逐渐走向多元共生。(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 陈 钢)